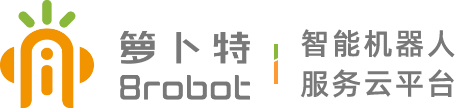于10月29日在艾厂人工智能艺术中心开幕的新展览《沙之书》再度将人工智能这一话题提了出来。在人工智能话题遍布科技与数码界、互联网、计算机等领域的近几年里,它得到了极大了关注,也收获了不小的误解。在任何可以插电的设备都可以冒用“人工智能”一词时代,也催生了不少艺术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创作,但与人工智能真正发生关系的作品及展览却为数不多,更缺乏精品。科技与艺术永远是人类文化进程的共生的两个翅膀,或许我们正处在一个人工智能艺术兴盛的时代。也正是这样,它受到了如同摄影技术当初出现时的些许质疑和排斥,也困惑着艺术家与策展人,在混沌中摸索着它的未来。
展览标题指涉的是博尔赫斯的小说《沙之书》(1975),在《沙之书》中,“他描绘出一个类似人工智能的非技术载体——一本能够生成万物的书,映射了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内核,即脱离技术的后人文主义:人类主体与其说是受到来自自身技术的威胁,不如说是受到来自机器的‘新主体性模型(new models of subjectivity)’(Katherine Hayles)的威胁。”这种危机感虽是众多科幻惊悚题材作品的核心来源,却在当下为创作者们提供了一个“甜蜜时刻”,即我们处在“新主体模型”对人类产生威胁的前夜之中,而这种威胁能否发生、何时发生,便成为了驱动创作者们利用新工具进行艺术创作的工具。
本次我们采访了参展的两位艺术家:大悲宇宙和 Sofia Crespo, 二人分别在展览中呈现了利用随机算法和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在大悲宇宙的《文本基因计划》(2018~2021)中,他展示了通过人机互动与机器学习生成随机语句的作品,在略微生涩的句子中,一种类似俳句的古怪美感被呈现出来。而他的《虚拟蝴蝶》(2019~2021)则通过人工智能,利用已有的原始材料与数据,不停地生成具有随机花纹的蝴蝶,并让观众进行放生。Sofia Crespo的作品也同样关注自然,她的《人造自然史》运用18世纪生物学插图的视觉语言,展示的却是通过算法生成的不存在的生物,或者按照她说的,是另一种可能的生物演化路线上的动植物。这几件作品并非单纯炫技性地体现人工智能有何种能力,而是通过艺术家的介入,让它们具有了展览想要呈现的后人文主义色彩。
展览现场二层空间
大悲宇宙
能否简单聊一下这次展览与策展人的合作过程?策展人是如何从您的众多作品中选择《文本基因计划》( 2018~2021)和《虚拟蝴蝶》(2019~2021)的?
跟艾厂的策展人合作是很顺利的,因为上面说到的两个项目都有涉及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技术跟理念,特别是《文本基因计划》。这个项目里面有一些关于语言的、关于数据的一些探讨,配合这次艾厂开幕展的主题“沙之书”真的蛮妙的。
在网站的《文本基因计划》中,除了访客输入的词汇之外,原始的基础语料库来自哪里?而此展览的这个版本中,语料库又是来自哪里?以及为什么选择该语料库?
《文本基因计划》的原始语料库来自于我平时的阅读收集,里面包含了很多学科的专业词汇,还有自从白话文运动以来我能找到的比较喜欢的现代诗。我把这些资料拆解成词或是短语,然后输入到算法里,这是最原始的版本。这次展览的版本加入了项目网站上线至今超过70000访客上传的文本,还有策展团队根据人工智能相关文献整理出来的语素语料。所以现在的语料库里不仅有我关心的,也有我身边人关心的,也有人工智能所关心的。
您在选择这些句子作为《文本基因计划》的过程中,会怎样进行考量?是选择一些完全符合语法逻辑的句子还是说要保留一些看起来比较“别扭”的句子?我的意思是,您的筛选动作,决定了作品呈现的效果,您想要让它看起来与人类无缝衔接还是略微生硬?为什么?
我在使用《文本基因计划》的网页交互页面时,通常会生成一些不符合语法或逻辑的句子,它们也被登在了网页上。这种略微生涩的句子其实呈现的是人工智能不太智能的那一面。
文本基因计划有三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文本基因库”即语料词库(上题有解释),第二部分“文本基因蓝图”(网页端的互动留言板),第三部分“文本基因组”(影像作品)。严格来说,只有第三部分有用到人工智能算法(GAN)去生成与文字内容呼应的画面内容,所以你提到的网页端也就是“文本基因蓝图”,其实用的算法并不是人工智能,而是随机算法。通过随机算法让这些中文语料像叠乐高一样随意拼凑产生大量的结果,再通过网页互动的方式让登录网站的人来阅读这些散乱无序的句子,让他们选择有意思的句子存留在网站上。
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现在AI在写东西这方面已经很厉害了,他们能够很准确地写出东西来。当所有语言输出都合乎情理、常规正确的时候,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丧失了很多没有想象过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文本这个领域里。随机算法带来的很多文本的不可读,但同时带来了非线性思维的文本输出。我在这些光怪陆离的文本里感受到了很美丽的东西。而当你在阅读这些文本并通过意识去筛选这些文本的时候,你某种程度上也变成整个项目算法的一部分。这有点像对抗生成神经网络(GAN)里的“鉴别者”。所以怎么说“文本基因蓝图”呢?或许它是以脑力、以人的意识力作为驱动的“人工”智能。
《文本基因计划》
这组作品有两个创作主体,一个是艺术家本人,另一个是计算机。观众可能关注作品“技术”或仿真性的那一面(计算机的功能性),评判句子或画面“真不真实”,也有可能关注作品的观念 (艺术家的功能性),去评判作品想要传达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如何平衡二者的?
终于要聊到真正人工智能的部分了,也就是刚刚上面我们有聊到的文本基因计划的第三部分,也就是这个项目的最终产物:文本基因组。简单来说,文本基因组就是我通过阅读大家遗留在网页端里的文本内容,加上自己的理解,之后整理出来的短诗,再配上GAN生成的画面与人声念白、配乐完成的影像作品。画面内容基本上就是诗歌里关键词的景物。这些图片源头来自对网络大量的图片训练,让算法模拟临摹出来类似的景物。所以回过头来聊“平衡二者关系”,我觉得在文本基因组的影像里不仅仅是二者而是很多“者”。从第一步文本库里就包含了非常多人的意识碎片,再到第二步通过随机算法产生结果,大家再次筛选文本内容,到第三步我自己的意识在大家两番处理过的信息基础之上又进行整理,又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再次进行了文本到图像的转换。这里面的步骤细节还有许多,我就不做赘述了。所以怎么去说“平衡”这件事情?当天平不仅是两边而是有无数边的时候,“平衡”这件事情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当所有构成作品的思维网格交织在一起,算力与脑力细细密密的缠绕的时候,再去剥离它们是否还有意义?
关于《虚拟蝴蝶》系列,您强调的是计算机的学习能力和虚拟演化,它们能够创作出比自然界还要多的物种,并且只要愿意,便可以持续不断地生成。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仿佛“上帝之手”的选择的角色(自然选择vs人工选择),这是否蕴含着一种形而上式的创作理念?人与计算机在这个生成与淘汰的过程中,达成了怎样的共生?
虚拟蝴蝶在我写这篇采访的时候已经突破了100万只。每一只都经过我的筛选,虽然里面也有“好坏”之分。算法生成出来的蝴蝶有百分之九十都会被我删除。基本上能够存留下的蝴蝶少之又少。也就是说,可能有将近900万只蝴蝶被我删了。我是基于什么标准去删除这些蝴蝶?最直白的标准就是欲望。欲望来源就是蝴蝶项目本身。大量的筛选跟蝴蝶各种造型纹理信息的灌入,时时刻刻都在改变我对蝴蝶美学的概念跟理解。当一个范式到达饱和视觉厌倦的同时,也在孕育新的渴望。就这样伴随信息与欲望的潮起潮落,当蝴蝶项目进入了一个正向循环数量增加的同时,蝴蝶的视觉信息也在日益复杂。
《虚拟蝴蝶》
在众多的物种中,选择蝴蝶作为主要客体的原因是什么?有无美学之外的考量?(比如植物也同样拥有变化丰富的形态和庞大的数量。)
在虚拟蝴蝶之前也尝试了很多创作方式,包括在未来也会去拓展的工作创作方式。但我在蝴蝶这个形式上探索了将近两年。不得不承认,蝴蝶在不同文明、不同文化里的认知拥有许多共性。三维的生物能够很好地在二维上呈现,在这一点上,没有其他生物能够出蝴蝶其右。仰仗在二维层面的优秀表现,其呈现在算力上也承接了这个优点。同样,在工作流程里,蝴蝶能够承载的信息够多在消耗算力上也很合理及优秀。
在此次展览的版本中,您将互动的主体交给了观众,让他们去选择蝴蝶“放生”,从而它们的数据被移除,这种颇有佛家思想和侘寂美学的做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准确来说是数据产生了转移,我从设备里传输到你设备里后,我这边删除掉原来的数据,所以这便是“无”吗?我觉得我更想让观众体会“有”。特别是在虚拟介质里产生“有”这个概念,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拥有。
最开始关注您的作品是佛像的系列,同时您的alias“大悲宇宙”和佛像及金刚像的作品也构成了一种悲悯且虚无的意象,可否简单介绍一下,在您创作艺术的初始,是如何将人工智能能、算法、计算机生成等要素结合到宗教之上的?
人是基于想象的才称为人。基于想象我们创造了太多太多,让我们有别于其他动物。包括对自身未来的想象。而宗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通过这些叙事,一代一代人口耳相传,激发我们对超我成神的渴望,用科学技术不断地去接近企及“神迹”。
《虚拟蝴蝶》展览现场
随着作为主体的人的参与越来越少,完全由计算机创作的艺术作品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威胁还是解放?为了体现人的创造性,在未来,艺术家是否会由创造艺术转为创造算法?可否简单地构想一下?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现在创作的生产工具(硬件,软件)跟生产物料(数据库),再到创作出来的作品,构成它们的条件很复杂,甚至有些跟我都很难产生关系,但不妨碍我使用它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创作。回过头来说,自动创作与未来艺术创作的问题。我在码字的同时在喝一杯茶,准确来说是岩茶。它属于乌龙茶的一种,如果要再细分,可以聊品种跟产区,但同样的茶树换作其他工艺可能就是别的茶,同样的工艺、同样的茶树,移栽到不同地理环境也可能变成其他的茶。环境、技术、茶树,这些就好比我们刚刚说的硬件、软件与数据库。当算法与科技、艺术相融合时,或许我们需要打开新的感知。品味其中的不一样,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在新的语境里找到新的叙事,就像上面我们聊到的,人类最擅长的就是想象,包括定义想象的想象。
Sofia Crespo
初次看到您的作品《人造自然史》时,它使用了一种非常逼真的视觉语言,就像是来自18世纪的植物学或动物学的百科全书插画一样。所以古典的生物分类学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基本上准确地概括了我们在照相机出现以前,是如何通过最初的植物学或动物学的观察来理解并体验周遭的世界的。这些探险家和科学家是在发掘物种的现场进行绘画的,并作出了最初的分类和归类,构建出一个又一个的物种,也成为了我们当下所继承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因此,这种对世界进行拆分并依据某种特征进行归类的方式,成为了我们构建现实的一种主导方法。
当然,这也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这种方法同时也是让我们理解并感受周围世界的关键要素。比如显微镜,它能够将自然界的事物拉到更近的眼前,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在肉眼看不见的尺度下的微观世界,因此,显微镜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在这一系列中,我对植物学和动物学早期的科学阶段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探索与冥想,想要探索那些在美学之下的规律、纹样和暗流。并且,这些构成生物学科的主体将生物学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它们曾经极大地丰富了生物学本身。
这些物种不光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美,更是通过揭示一些我们习以为常和司空见惯的要素,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并且能够同时让我们找到那种发现奇迹的喜悦,那种在自然界的边界发现未知的欣喜。
《人造自然史》
通过将古典的视觉语言和最新的科技结合,《人造自然史》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被创作出来,它创作了一种“另一时空”的自然史,或者说,自然史的另一种历史轨迹。您可以详细地阐述一下创作的思路吗?
对我来说,使用新科技让我达到了很多“用手”创作所做不到的事情。相关的算法帮助我从我创建的数据库中提炼视觉的精髓,并且更能让我直观地窥见另一种可能的历史并对其进行探索。这种平行的历史对我来说就像是我们已知宇宙的一个镜像或放大镜,我们无法参与其中,但是却能够沿袭它的文化和制度。另外,当我们与其相与的时候,能感受到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似乎看到了另一种更加迷人的潜在可能性,以一种全新的更丰富的视角去看待,进而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自然世界。
当电脑生成图像之后,您做出选择(自然选择vs人工选择这一层面)的标准是怎样的?自然会淘汰掉那些无法适应的突变,那么在您的选择过程中,您的动作就成为了物种存留或淘汰的要素。可否简单聊一下,除了美学因素以外的做出选择去留的因素?
能够从单一的数据库中生成大量而繁复的物种,运用随机算法,让我能够从大量的生成的图像中去主动选择。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并不是仅仅关于美学的,主要的工作在构建数据库上、调研工作、探索、创造,以及挑选,这些工作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要素,也正是这些工作让我不断地质疑我自己是否带有某些偏见,比如对于已有的数据库,我是否有哪些偏见或偏向,在平衡能够代表自然界的物种时,我是否能够做到平衡。
《人造自然史》展览现场
您对于《人造自然史》有哪些未来规划?会出版一本总结性的书吗?会以纸质书的形式出版一本关于“假的”生物的百科全书吗?
我目前正在创作《人造自然史》一书,将对另一种宇宙、神经现实的观察整理成精彩的物种典藏,用大部头的方式比较符合,而不是用一系列印刷书籍的形式。
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艺术中扮演的角色?随着人类在艺术创作中的参与越来越少,人工智能即将扮演的是一个解放者的角色还是威胁者的角色呢?那么,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参与变得更多,艺术家在此过程中是不是担任了一种更接近策展人的身份了?
对我来说,人工智能在当下或者能够预测的未来里,仍然只是一种工具,能完成画笔或者照相机无法实现的工作。就像其他的所有数字工具一样,代码也好,算法也好,它们只是对创作过程的一种增强,能够让完全无法实现的创作过程变为可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数据库中拥有成千上万的图像,一旦它们经过了学习训练,神经网络便可以生成无数的新图像,进而探索数据库中的核心本质,用一种十分直观的方式与我的创作过程和思路相结合,与自然世界产生反馈回路。
那么您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让作品凸显个人色彩,或者说是克雷斯珀式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是又非常难回答。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我的作品代表着我的个人偏好和兴趣,逐渐构建处理工具的过程以及对自然世界的理解方式、参与方式、直觉都让这些作品充分体现出了我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的输出。
您对于生物学的痴迷和对于真实世界物种灭绝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担忧?
我十分坚定地认为,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更强烈的创造共情的方式,对自然和居住其中的非人类生物产生更多的共情与悲悯。想要做到这一点,有无数的方式方法,但对于我来说,通过创作和探索艺术、数字媒体,在数字空间里创作自然的体验,并反过来,让我们对真实世界产生共情是我个人的一种做法。我们几乎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潜入海底去近距离观测珊瑚,或者让所有人都体验到第一手的关于雨林的深度或海洋及沙漠的生物多样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培养和促进人们去产生共情,让人们对多样的生物和生态系统产生好奇和关怀,而我坚信,艺术能够做到这一点。
汽车行业应用BI,应该从哪个环节入手?
2025-01-10【走近匠人】周顺平:学无止境,方能成就匠心!
2025-01-10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领航峰会”大咖观点集锦
2025-01-10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未来峰会”大咖观点集锦
2025-01-10社区智能化解决方案
2025-01-04智慧医院解决方案
2025-01-04打造智能化小区解决方案
2025-01-04